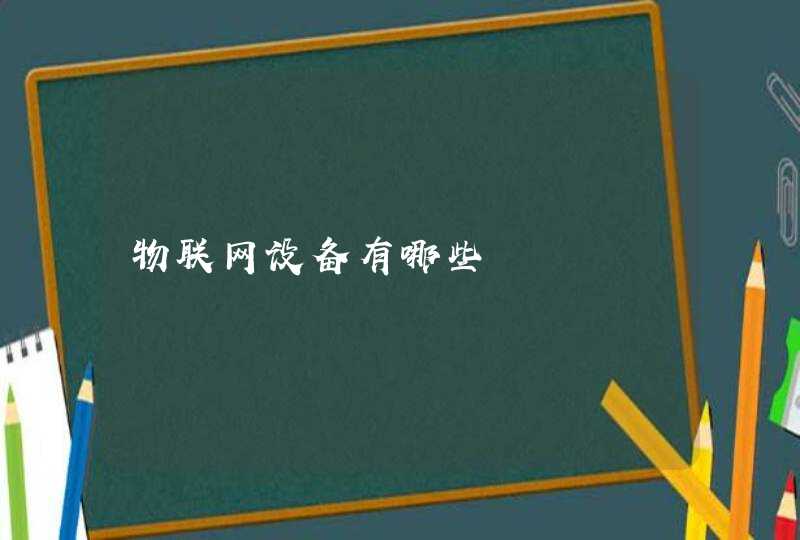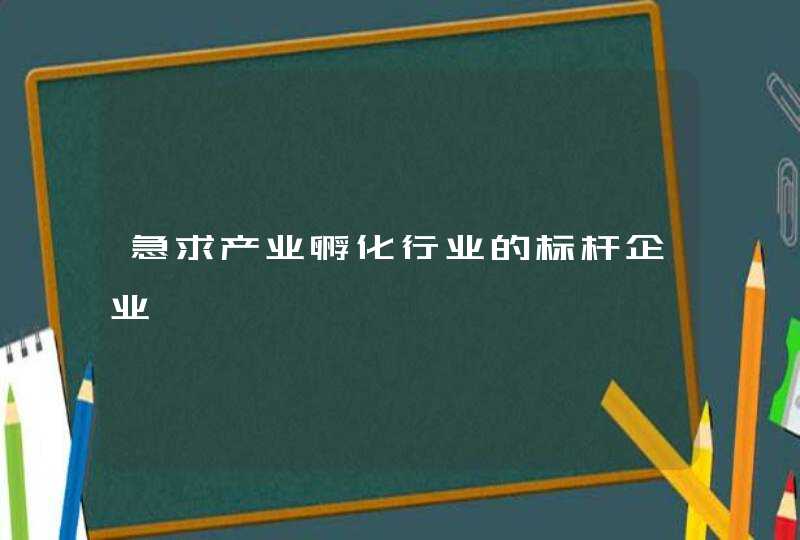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震动了国内外学术界,它为世界提供了一门新的学科——敦煌学。藏经洞发现的5万多卷敦煌遗书,实际上是一座中世纪文库,胡适曾称它为“和尚图书馆”。近百年来,各国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敦煌遗书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学者们发现敦煌遗书不仅对中国史的研究,而且对世界文化史的研究都起到或将要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许多历史上的重大疑难问题可以在敦煌遗书的研究中获得新的启示。因此,研究成果大批涌现,在国际学术界形成了所谓“敦煌热”。但是,现在你若想看看藏经洞发现的敦煌遗书,那么你必须跑遍全球。由于西方盗宝者的劫掠,使这些文献分散在十几个国家、30多个博物馆中,现藏我国北京图书馆的敦煌遗书不过是被劫后剩余的残卷。敦煌遗书中的精品流散海外,它给中华民族文化财富上造成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
一
据著名书画家、鉴赏家谢稚柳记叙:清光绪年间,敦煌寺院,王道士雇了一人在莫高窟七佛殿替他抄经。抄经人把点旱烟的芨芨草似芦苇插进墙壁的裂缝里,发现壁内深不可止,用旱烟杆敲壁,似有空声。王道士用镢头刨开墙壁,发现有一小门,又刨开泥封的门,是一间复室,约丈余见方,内堆积有许多白布包裹,每一包都包着经卷,整整齐齐,白布包下铺着经幡、绣像等等。这就是后来举世闻名的敦煌莫高窟藏经洞。
王道士愚昧,不懂这些文物的价值。他拿了些经卷、画像送给敦煌县知事汪宗瀚。汪是识货的,但他仅仅把这些东西当做鉴赏的古董、官场结交的礼品。1902年,甘肃学政叶昌炽从汪那里看到几卷古书,几幡画像,叶昌炽知道这批文物的价值,就建议当时的藩台衙门把这些文物运到省城保管。藩台衙门算了算,把这些古物从敦煌装车运到省城,至少得花费几千两银子,太不值得,没有采纳这个建议。但公事总得敷衍一下,于是藩台衙门给敦煌县衙下了一道公文“经卷佛像,妥为封存”。县衙接到公文,又下了一道公文给王道士,责成王道士“妥为封存”。历史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一大批稀世瑰宝的命运掌握在王道士手中,而堂堂满清政府的各级官吏却对此无动于衷。
王道士当然不会“妥为封存”,他带了一箱经卷到酒泉,呈送给安肃道道台满人廷栋。但廷栋不识货,以为这些缮本经卷的书法还不如他的好,只是拿了随便送人。恰巧,嘉峪关税务司有个比利时人任满回国,向廷栋辞行,廷栋送他几本缮本书,还告诉他是敦煌石窟发现的古书。比利时人路过新疆时,又把这些古书分赠给新疆的长康将军和道台。敦煌藏经洞遗书的发现就这样传播开了。
二
自1840年鸦片战争英帝国主义者用大炮轰开了中国大门之后,西方的所谓学者、传教士、考古学家、探险家纷纷深入到中国腹地,打着传教布道、测绘地图、勘察地质、调查民俗、研究方言等等幌子,肆无忌惮地无孔不入,疯狂掠夺我国大量的珍贵文物。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在劫难逃。
我国著名学者郑振铎1956年访问苏联时,在列宁格勒参观了冬宫博物馆,并到东方研究所阅其所发现敦煌卷子多至万卷,甚为兴奋。
这上万卷的汉文古抄本,一定会有惊人的发现。他“已经发现了两卷‘维摩诘变文’,又看到了‘刘知远诸宫调’……,皆是早欲见之,今始偿愿者……”郑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今天上午,续看敦煌卷子。共看了二三百卷。都是他们事先挑选出来的;未被挑选的,不知还有什么‘宝物’在内。就这几百卷东西内,已有不少十分惊人的……。”列宁格勒东方研究所收藏着约12000件敦煌藏经洞遗书,是1905年10月俄国人奥布鲁切夫和1914年奥登堡从敦煌窃去的。奥布鲁切夫在敦煌如何窃走经卷的,如今已无人知道,其实他是第一个到达藏经洞的西方盗宝者,早于英国的斯坦因二年。当后来另一个俄国人奥登堡到达敦煌时,藏经洞内遗书已所剩无几,奥登堡在向王道士收买的同时,还到附近居民人家搜购,得到不少精品。具体情况,奥登堡在他的旅行手记中作了记录。这份记录现藏原苏联科学院档案馆。倘能公诸于世,或许能告诉人们他和他的同胞在敦煌窃取遗书的情形。
三
1879年,匈牙利地质调查所所长洛克济和斯希尼到我国西北甘肃一带调查地理。洛克济到了敦煌,莫高窟无与伦比的精美壁画和塑像使他叹为观止。莫高窟留给他的印象实在太深了,乃至事隔20多年后,在1902年德国汉堡召开的国际东方学者会议上,他做的关于敦煌佛教艺术的报告,对莫高窟的壁画、雕塑的精致、美丽的价值推崇备至。他的“热烈的叙述”使得在座的一人垂涎三尺,心驰神往。此人就是斯坦因,也是个匈牙利人,但却在英国殖民地印度政府的西北边地担任总视学,后来又转入印度的考古学调查所。他在做了充分的准备后,两次到了我国新疆,当他从比利时人那里知道敦煌发现遗书,便迫不及待地在1907年5月赶到敦煌。
斯坦因是著名的梵文学者,虽然看不懂汉文,但他雇了翻译湘阴人蒋资生。斯坦因在他的《西域考古记》里说:“从王道士所掌微暗的油灯光中,我的眼前忽然为之开朗。经卷紧紧地一层层地乱堆在地上,高达10英尺左右。据后来的测度,将近有500立方英尺。小室约有9英尺见方……”除了缮本卷子之外,还有“用无色坚韧的画布作包袱的一个大包裹,打开之后,全是古画”、“颜色调和,鲜艳如新”。他不露声色地暗暗观察王道士,他看到王道士对这些宝贵的经卷和艺术品毫不在乎,很为“惊异轻松”,他想“到了这一步,热烈的心情最好不要表露太过”,果然,“这种节制立刻收了效”,“道士对于遗物的漠视因此似乎更为坚定一点”。
斯坦因窃走的遗书共一万余卷,还窃走了许多绘画、刺绣、绢画,其中有长及丈余、宽到五六尺的唐绣观音像,有木版雕刻印刷的金刚经,经卷上有精致的佛像,这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印刷品,最早的版画艺术杰作。斯坦因付给王道士的代价是14块马蹄银。这14块马蹄究竟是多少两银子呢?据《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上说约合720两,十六进位制。16个月后,这批中华民族的国宝被陈列在伦敦的不列颠博物馆。
四
接踵而来的是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他当时率领一支探险队在我国新疆进行考古发掘,当他看到长庚将军送给他的一卷佛经是唐代写本后,便迫不及待地问明来源,于1908年3月赶抵敦煌。伯希和是学识渊博的汉学家,他凭着深厚的汉学功底和丰富的考古知识,把藏经洞中所有的遗书通检一遍。他自己说:“洞中卷本未经余目而弃置者,余敢说绝其无有。”有一张伯希和盗窃藏经洞遗书的自拍照:他蹲在洞窟里,面对堆积如山的经卷,正在蜡烛下一件件、一页页地翻检……他在藏经洞里待了3周,“不单接触了每一份文稿,而且还翻阅了每一张纸片”。他纯熟的汉语基础和中国历史知识,使他选走藏经洞里的全部精华。所以,他盗走的经卷是最有价值的。比如有关道教经典的卷子几乎全被伯希和盗走了,大约有六七十件全部收藏在巴黎。敦煌遗书最大的价值是保存了许多古代学说,保存了古注。比如《论语》,现在读的只有一种本子,即何晏注的本子。藏经洞发现了皇侃注的本子,收录了两汉和魏晋之间所有人讲《论语》的要点,都被伯希和盗走了。伯希和自己也曾自诩说,他拿去的卷子在敦煌卷子里几乎都是最有价值的。他把斯坦因依靠翻译而忽略的更珍贵的经卷和语言学、考古学上极有价值的6000多卷写本和一些画卷,装满10辆大车,运往巴黎。
五
继奥布鲁切夫、斯坦因、伯希和之后,1911年10月,日本大谷光瑞率领的探险队也到过敦煌,成员中有桔瑞超和野村荣三郎,他们从王道士手中骗到500多卷经卷和两尊精美的塑像。
1909年5月,伯希和再度来华,他为了向中国学者炫耀自己取得的辉煌成果,将随身带来的敦煌遗书在北京六国饭店展出。中国学者罗振玉、董康、蒋斧等人闻讯,拜访了伯希和,伯希和向他们通报了敦煌藏经洞的情况。据罗振玉记载:“博士指伯希和为言石室尚有卷轴八千轴,但以佛经为多,异日恐他人尽取无遗,盍早日购致京师。”《集蓼编》中国学者这才看到几卷敦煌遗书,“摩挲赞叹,扼腕不已”。当时的《顺天时报》、天津《大公报》也以“石室藏书出现”为题进行报道,敦煌发现“藏经洞”的消息这才传遍京城内外。清政府到这时才如梦初醒。
1909年8月22日,在敦煌藏经洞被发现的第9个年头后,清政府学部教育部才发出电令,并拨经费6000两白银,令搜买敦煌遗书,敦煌县存档的第47号《移文》中记载:“奉学部搜买,敝县会同学厅传及绅民,尽其洞中所存者一律搜买,护解省垣……搜买千佛洞前代写本经卷解省,领价改修文庙。”1910年三四月间,敦煌县将第一批敦煌遗书6004卷装车启运。这批劫后的遗书自敦煌运至北京途中,因偷盗而散失无数。当运送遗书的大车抵达北京时,新疆巡抚何彦升字秋辇之子何震彝字畅威竟将大车接到自己家中,约其岳父李盛铎字本斋和刘廷琛、方尔谦等人,挑选遗书,取其精好者藏匿下来,而将较长的经卷,一拆为二三充不足之数。根据李氏及家人以后出售的卷子目录,看出李盛铎当时攫取四五百卷,何震彝藏掖得更多,因他死得早,又将经卷大都作为礼物馈赠了亲友,所以何氏究竟拿走多少至今是个未知数。现藏东京的一部分卷子,现藏台湾中央图书馆的150余卷经卷,就是何、李当年私下藏掖下来的。对于这种明火执仗的偷窃行为,学部侍郎宝熙上章参奏。因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土崩瓦解,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总之,这批敦煌遗书在1910年入藏京师图书馆时,卷数比敦煌起运时还多,变成8697卷。1929年,京师图书馆将卷移交北平图书馆时,则成了9871卷。如果以卷数而言,现在的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已近万卷,成为世界上著名的收藏敦煌遗书的三大图书馆之一了。
六
自1900年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经卷之后,1944年,常书鸿先生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以外的地方又发现了经卷残片。1944年8月30日,他们在莫高窟中寺后面的一座小庙移动三尊清末价值不高的塑像时,由于塑像里面的木棒埋在土台基座下很深,所以无法移走。因此只好毁掉塑像,拆毁后发现,塑像里包裹木棒的材料既不是草,也不是芦苇,而是写有经卷的残片。常书鸿和考古学家夏鼐、敦煌学专家向达等人一起进行鉴定,共发现经文66件,残片32片。这是继藏经洞发现以来的又一次重大发现。拆毁的三座塑像,在1900年藏经洞发现之前就已存在了,可见这些写经不是藏经洞里的经卷。从纸质和字体上看,是六朝的遗品。这说明在莫高窟藏经洞之外,也有发现写经的可能。敦煌莫高窟今后一定会发现新的藏经洞,而且是不容置疑的。
一个半小时以后当萨宁回到路塞里糖果店时,他在那里受到亲人般的接待。爱弥儿坐在给他刷身的那张沙发上;医生给他开了处方,建议病人“小心自己的感觉”,因为他这个人的气质是敏感型的,很容易得心脏病。他以前也曾有过昏厥,不过从来没有发得那么久,那么厉害、好在医生说一切危险已经过去。爱弥儿的穿着像一个正在康复的病人,套着一件宽大的睡衣;母亲在他脖子上围了一块天蓝色的三角头巾;但是他的样子非常快乐,几乎像过节一般。再说周围的一切也都呈现出一派过节的样子。沙发前面放着一张圆桌,上面铺了一块干净的桌布,高高耸立着一只盛满香喷喷的巧克力的大瓷器咖啡壶,壶四周摆着茶盏,盛糖浆的长颈玻璃瓶,饼干,小圆面包,甚至还放了花;六根细细的蜡烛分别在两只古老的银烛台上点燃。沙发的一头是一张伏尔泰椅,正张开自己柔软的怀抱,萨宁正是被请在这张椅子上就座的。糖果店里在那一天他必须认识的一应人员,都到场了,连狮子狗塔尔塔里亚和猫咪也不例外。大家看起来都说不出的幸福。狮子狗甚至高兴得打起了喷嚏,只有猫咪还是装腔作势,眯着眼睛。萨宁被要求说明自己是哪里人,从哪里来,姓甚名谁。当他说到自己是俄国人时两位女士有点惊讶,甚至啊地叫了一声,但是马上又同声说他的德语说得非常好;不过,假如他觉得说法语更方便的话,他也可以说这种语言,因为她们两人对法语的理解非常好,而且也说得不错。萨宁当即接受了这个建议。“萨宁!萨宁!”两位女士怎么也没有想到俄罗斯姓氏的发音竟如此轻松。他的名字“德米特里”也使她们很喜欢。年长的那位女士说,她年轻时听过一个歌剧叫《德米特里奥和波丽比奥》,但是“德米特里”比“德米特里奥”念起来好多了。萨宁以这样的方式闲谈了大约一个小时。从自己方面说,两位女士也向他叙说了自己生活中的一切详情。说得更多的是母亲,那位头发花白的女士。萨宁从她的谈吐得知她叫来诺拉-路塞里,在丈夫乔万尼-巴蒂斯塔-路塞里去世以后一直守寡;她丈夫二十五年前作为糖果点心师迁居到法兰克福;乔万尼-巴蒂斯塔是维琴察人,虽然性情急躁,也有点孤高自傲,为人倒挺不错,而且,还是个共和主义者!说到这里路塞里太太指了指挂在沙发上方的那幅他的油画肖像。应当认为画像的作者(正如路塞里太太指出的那样:“也是个共和主义者!”)没有能完全抓住他的形貌,因为画上那个已故的乔万尼-巴蒂斯塔像个神色忧郁冷峻的绿林好汉,类似里纳尔多-里纳尔第尼①的人物!路塞里太太本人出身于“古老而美丽的帕尔玛城,那里有不朽的柯勒乔绘画的美妙绝伦的圆顶②!”
高延明:男,1981年出生,中国国籍,大学本科学历,中共党员,仪器仪表行业高级工程师。2009年10月起就职于汉威科技,历任市政燃气事业部总经理、郑州畅威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等职务,现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公司副总经理、嘉园环保有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以上就是关于藏经洞的文物是怎样流失到海外的全部的内容,包括:藏经洞的文物是怎样流失到海外的、玉白菜进门的时候打破了是什么预兆、高延明年收入多少汉威科技副总经理等相关内容解答,如果想了解更多相关内容,可以关注我们,你们的支持是我们更新的动力!